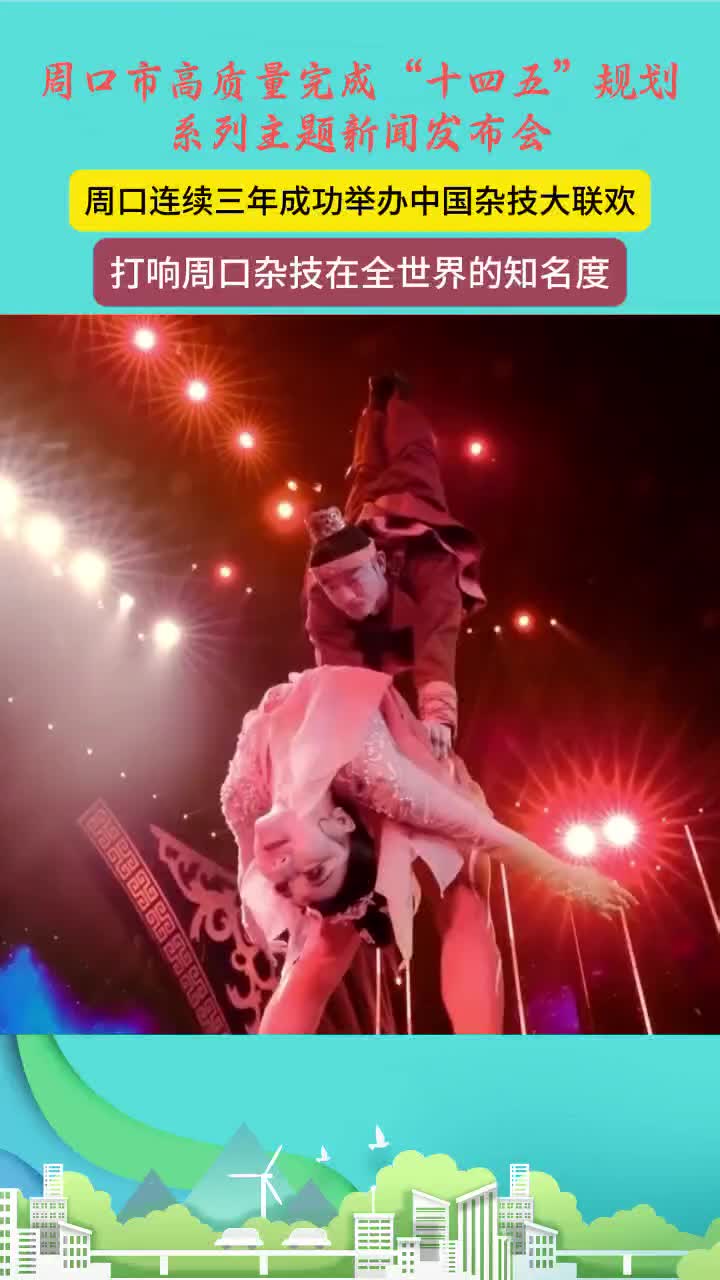生活有味,人间值得
郭文艺
一
门前的花池空着,已有些时日了。
先前这里是个美容店,店主是个爱穿白裙、一笑露虎牙的女士。她喜文雅,酷爱养花。春天,一把花锄,将三个花池整得平平整整。
月见草、虞美人、一串红、鸢尾、矮牵牛……这众多花间,当数小凤仙花期最长,红红火火,像一群朝气蓬勃又不失温柔的少女。常常是到了霜降,门口依旧热闹。身上点缀“墨汁”的大花蝴蝶时常来池子间飞舞,赶闲集的人们走累了,台阶上一坐老半晌,只为贴身欣赏这些粉红色的小精灵。
一连五六载,年年如此。
而如今,美容店易址,店主不知去向,这些个花池子无人打理,高贵娇嫩的花草被一片野草蹂躏,渐渐失了本色。
我又是个粗人,每每观之,亦只能暗自叹息。
绵绵的秋雨终究是停了。见天儿,母亲说,在花池里种些蒜瓣子吧,可以吃蒜苗,总比荒着强。母亲蹲下身子去刨土,清理枯草,我往土里放蒜,一行、两行……
过了一周,满池子又恢复了热闹。青绿青绿的苗芽破土而出,迎着朝阳,一片生机。
谁家吃饺子,母亲乐意招呼他来割头茬蒜苗尝鲜。
如此,花池变菜园,既不失土地的意义,又为生活增添些趣味,值得。
二
我一向对“五更”不辨,弄不懂子、丑、寅、卯的具体时段。
可巧,河畔林间来了养鸡的人。搭帐篷,围栅栏,几天的工夫,住宿有了,鸡圈也成了。
圈里除鸡外,有鸭、肉鸽,也养鹅,热热闹闹的一大群。每日里放学归来,小儿立贤必先站在栅栏外看一阵子,有时候到超市买面包,总拿两块。我问起,便答,爸爸,我吃一块,喂鸡鸭鹅一块呗。
夜里,听鸡叫。头遍睡得正熟,猛然一声清凉的鸣啼划破寂静,梦就此打断。
被子蒙头,专注地猜是哪一只大公鸡叫得正欢。翻个身,继续熟睡。
至天亮,又是一阵鸡鸭鹅的混合叫声。这会子脑袋清醒了。不知怎的,每听这声音,总能想起多年前的老宅院:一声接一声的鸡鸣里,祖母站在灶屋里熬粥,祖父劈柴,隐隐约约,看见父亲扛铁锹正往北地走……
鸡养大了,用红绳绑住腿,放桥头供人挑选。极个别的孤寡老太太会挑选一只体型矫健、精神十足的柴鸡抱回家打鸣。大多数年轻人买了去做下酒菜。喝酒的人付了钱要杀好剁块儿,用黑塑料袋子提回家炖。女主人佛性禅心,把鸡摁在案子上,口中默念“小鸡小鸡你莫怪,你是餐桌上一道菜”,许是这样念能壮胆,而后手起刀落,鸡头便离了身躯。
褪毛,去五脏,小鸡瞬间成了一堆肉。
女主人在杀一只鸡时,圈里其他的鸡眼睛都直直地朝这边看,它们或卧或站,交头接耳,有几只上蹿下跳,尽显惊恐状,仿佛眼前的一切,令它们至死不解其中意。
转念想,人这辈子三万多天都解不开生老病死之困惑,何况一群鸡鸭鹅呢。想来,宇宙之大,自有其规律可循,凡事顺其自然,亦不必妄为解之吧。
人呐,侥幸托生为人样,自当珍惜生命、好好生活才是。
三
冬初,许多树落尽了叶子。
我穿过几条巷子,去寻找三爷,在一处骨牌摊子上,瞧见了他。
“三爷,您找我?”我喊了他一声。三爷回头见是我,站起身,乐呵呵地抓起桌面上的几枚硬币,叫我跟他走。
到了他的红砖灰瓦的小院落,三爷搬出一条长凳,右手从上衣口袋掏了根烟,点上。
“人老了,记不清楚了。上回通知的医疗保险,我给忘了,今早猛地想起,才慌忙叫人喊你来。你们年轻人,都懂手机,帮我交了吧。”我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,也就两三分钟,便完成了三爷的托付。
三爷起身,走进了屋,片刻,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几张皱巴巴的票子递给我。
“三爷,这钱您先拿着用呗……”“不,我有。”三爷摇头,目光坚定,把钱塞进了我的裤兜。
两个人坐在堂屋门口晒太阳。八九十岁的老人,身板硬朗,说话响亮,耳朵好使,眼也不花,是难得的好事。
太阳底下,我听三爷聊起往事。三爷左看看我,右看看我,忍不住笑道:“越看你越有你父亲当年的样儿。”“啥样?”我问。“为人和善,脾气又倔强呗……”也是,可见当年父亲取大名叫郭喜善,是有他的道理的……
三爷继续搅动着整个村庄的乡愁,满脸的皱纹在讲述时错落交织,像一道道被岁月河流冲刷过的痕。
三爷,一个独居老者,一个濒危的时代纪录碑,一个我们珍爱的乡愁记忆体……
而此刻,我正坐他身侧,做时代的聆听者, 当乡愁的复述者。
何其荣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