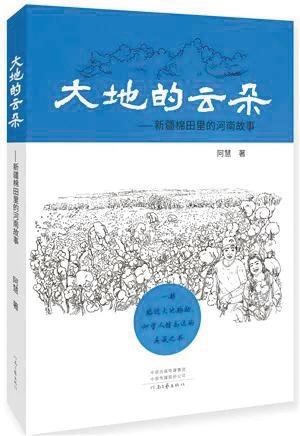□阿慧
(接上期)
一车人回到住处,老板娘和一个当地妇女,已经做好了晚饭。简易棚里两口冒烟的大铁锅,一锅面条,一锅开水。拾花工们端来盆子,舀热水泡手、洗脸、烫脚,没有多余的水洗澡,手和脚必须得泡一泡。“酒窝姐”说,一天下来手指头都是硬硬的,摁到热水盆里泡软乎了,才能拿筷子吃饭。
大家伙儿端着饭碗盛面条,我伸头朝锅里看,面条已熬得只成面,不成条,一锅粥似的。大家端着碗蹲在墙根喝面条,呼噜噜一碗,呼噜噜又一碗,喝得脸上汗津津的。我仍就啃馍馍,这次脸皮厚了些,吃一个拿一个。老板娘给我冲了一茶缸鸡蛋水,我感激地接过来,一口气喝下去,肠胃一路快乐地叫。这鸡蛋水,怎么品都比在家时好喝,这还是鸡蛋吗?天鹅蛋才是这个味道。
“酒窝姐”手拿一个紫红的洋葱,一层层啃着吃,嚼得咯嚓咯嚓响。
她说:“这皮芽子就馍很好吃,你试试。”
我纠正说:“这是洋葱。”
她笑,指指那个新疆女人说:“跟她学的,新疆人都这么说。”
我说:“咦!才来了几天连文化都融合了。”
“酒窝姐”没接话,新疆女人走过来,扇动着长睫毛问:“你俩说我撒呢么?”
我忙站起来对她说:“俺俩撒呢也没说么。”
老板娘给我收拾好了一个单间,我说要和姐妹们一起住,老板娘把我拉到一边,小声说:“那可住不得,没有下脚的地方。”
我说:“不会吧,我试试。”
一迈进门坎,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扑来。我止住脚,抬眼看,一个五六间屋子长的筒子房,没有一扇窗户,紧靠两边墙,一拉溜摆放三十多张高低床。中间的过道,满地都是盆盆罐罐,还有纸箱和鞋子。还有人,双脚泡在盆子里,湿了一片地皮。
见我进来,有人招呼说:“来来来,坐坐坐。”连连拍打着身边的床铺。床铺花花绿绿,堆着各色衣裤。“酒窝姐”站起来,拉着我的手说:“坐我这。”
我在“酒窝姐”床边坐下,气味有些浓度,有些复杂,我在田间采访时就闻到了。记得当时我问:“那你们怎么洗澡啊?”
大妹子说:“洗啥澡?在哪儿洗?没洗过,用毛巾抹抹就妥了。”我问:“你们来这多久了?”
她翻着眼皮一算,说:“明天整四十天。”
听到这,我又立刻站起,来回走两步,拿定主意坐下,掀开大姐的被子,狠狠地说:“我今晚就跟你们睡了。”
姐妹们一个不小的意外,我也意外地得到两个酥梨、三个苹果、一把葡萄干。
我边吃边酸酸甜甜地说:“你们比俺老公还疼我。”
送葡萄干的女子说:“那俺比不上你老公,他给的东西俺可给不了。”
大妹子骂她说:“你个没出息的货,又想老公了吧。”
葡萄干女一撇嘴说:“你不想? ”
大妹子魏桂花扭头看门口,说:“不知道。”
她一说不知道,大家伙都“哦”了一声,说:“知道了。”
我还没有悟过来,问:“知道啥了?”
大家一起笑起来,“酒窝姐”点着我说:“妹子你白喝了一肚子墨水子。”这下我也知道了,伸手点了一下她脑壳,她也点了我一下,一屋子女人笑得东倒西歪。一时间,我感觉就像坐在河南老家那光溜溜的打麦场。
姐妹们渐渐沉入梦境,我无法入睡,身子酸痛得难受。听见小老鼠在地上窸窸窣窣;听见屋外的风呼呼呜呜。
对面下铺的姐妹,突然翻一个身,伸手朝旁边抓,嘴里说:“抓呀、抓呀、抓不动,哼哼……”
把邻居抓醒了,“啪”地打了她一巴掌。
“酒窝姐”在被窝有响动,一声又一声,我捂紧被头,憋住,不呼吸。终于憋不住了,深吸一口气,是不太新鲜的皮牙子味儿。
李大义老板在外边喊时,我才找着睡觉的感觉,只听他突然一嗓子:“起来吃饭啦!快起来!”
有人气得直哼哼,说:“周扒皮。”意思是说,李大义就像《半夜鸡叫》里那个坏心眼的老地主。
“酒窝姐”起身穿衣服,朝她“嘘”了一声,说:“别让他听见。”
大家闷闷地起床,走路还在睡梦中,我也跟在后面摇摇晃晃,像踩在棉花包上。
摇晃到屋外,更像是梦境了,天黑洞洞的,土坑里的芦苇影影绰绰。
我一夜没暖热,出门打哆嗦,寒气上来抱住腿,顺腿向身上走,浑身立马凉个透。
老板李大义威严的身影清晰可见,他站在厨房棚子的灯光下,一手夹烟,一手掐腰。那烟头一红一灭,一股烟儿刚吐出,就被冷风扯走了。
从北边一排土坯房,陆续走出一群姐妹,我都不认识。李大义说:“这是二队的,昨天你采访的是一队,每个队也有六十多号人。”
这时,十几个男同胞也从东南角宿舍里出来了。他们在老板的注视下,洗脸,吃饭。半锅炒白菜,一笼大馍馍,一锅热面汤。
没有见到老板娘和帮厨的新疆女人,李大义吐出一口烟儿说:“她们忙午饭和晚饭,早饭我来做,让她们休息会儿,一百三十口子的吃喝,也够她们累的。”
李大义对我说:“无论饭菜好坏,我都让大家吃热的,凉菜不敢做,馍、菜、汤都放在煤火边。他们出去得早,回来得晚,这天那么冷,人都冻透了。”
果然,热饭吃到肚子里,寒气就不敢近身了,人开始有力气说话了,白烟从嘴里一股股冒出来。
(未完待续)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