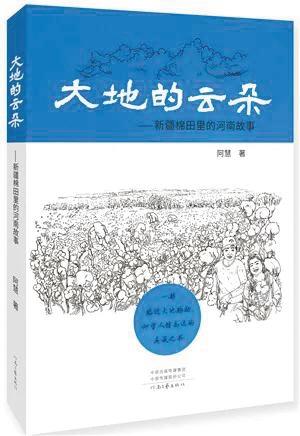(接上期)
我听得直冒汗,说:“你这爹当娘使,当得比娘都用心。”
我问邓大哥:“现在你的孩子都有孩子了,该为自个儿考虑了,怎么不找个老伴呢?”
他说:“这二十多年,不少人给我提过亲,可我一个也不见。你想啊,亲娘都跑了,后娘能靠住?后来,我把孩子们操持成家了,自个儿更不想找了。人家有德有望的好女人不肯改嫁,改嫁的又都看重彩礼。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,就想图个清净,不考虑这事了,就这样安安生生地过日子吧。”
“安安生生过日子”这是邓大哥最真实最朴素的人生愿望。
我说:“热也好,冷也好,平平安安就是好!”
这时,邓大哥朝西面一指说:“杨老板来了。”
一辆摩托车搅起一股田野的风,沟渠边的尘土散开又聚拢。我远远地见他下了车,瘦长的身影在地头虚飘。杨老板停下突突叫的摩托车,就像在田埂上栓好一头活蹦乱套的驴。他从后座费力地拎下两只大饭桶,见拾棉工纷纷走来了,他转身走向远处的小榆树,蹲下,点上一支烟,两条长胳膊抱紧腿。
大家伙儿各自盛饭,取水,拿馍馍,围坐一起吧唧吧唧地吃。我拿一个大馍馍一点点揪着吃,不吃菜。改换了一只锅,我心里过不去。飘来一股股炒萝卜味,这菜味很熟悉,我在月清嫂家亲手做过,想来杨老板家,也种了一院子的清脆大萝卜。“憨女子”柳枝儿蹲在我前头,她把大半个馍馍泡在菜汤里,却从碗底使劲往外刨菜吃,她刨出一筷子粉条给我看,嘿嘿地笑说:“细粉!还有细粉哩。”我朝菜桶看,见一半萝卜一半粉条,不是稀汤寡水的那种,就朝厚道的杨老板投去感念的目光。
杨老板始终没有扭头朝这边瞅,他静静地蹲着,我少见这样的地老板。就想,他对拾棉工是懒散中的放纵?还是放纵中的懒散?他是焦急这眼前没开好的棉花,还是焦心家里即将落花的妻子呢?都有吧,这彻骨的寒,冰封了这男人的心和口,在寒风中,他紧抱着自己的双腿取暖。
收拾好自己的碗筷,拾棉工匆匆走向各自的棉花垄,杨老板摁着膝盖站起身,脚步有些摇晃不稳。我把歪倒的空桶提起来,递给他,他伸手接住,没有说话。蓬乱的黑头发,缺乏睡眠的双眼,深眼窝里住着寒风。望着他骑车而去的瘦弱背影,我想说,朋友,这只是一场意外,一切都会过去的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我走回棉田时,他们正谈论杨老板。
“玫瑰女”陈银行说:“我本来想好了,要对他说两句难听话。看他这棉花,猛一看一片白,拾起来可费劲,棉朵开得像蒜瓣子,抠得我手指头直冒血。天不亮就来了,到现在还没有抠满一袋子。要是在其他地里干,能多抓一半的钱。可是我一见杨老板那作难的模样,就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。”
“指甲姐”付二妮说:“银行你不说就对了,有些话说了就收不回来。人家老板日子遇上了坎儿,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,他地里的棉花,趁雪还没下,咱拾回去一点儿是一点儿。别说人家按斤付咱钱,就说一分钱不给,咱也不忍心抛洒这神物。你看这白丝丝的棉花,是天神给咱的金丝、银线、身上衣,金贵着哩,糟蹋了有罪。”
我有些明白了,“指甲姐”付二妮,八个手指甲都磨掉,但她没有停止拾棉花,这都是为什么。我观察过,“指甲姐”拾过的棉垄最干净,几乎不落下任何一朵花,棉壳上没留丝丝缕缕的“眼睫毛”。她不仅是跟自个儿的指甲过不去,跟白花花的银子过不去,她其实是跟爱物稀物的本性过不去。她不知道“暴殄天物”这个成语,却把它化成空气,化成水,融化在她心里、魂里、日子里。她和无数个农民兄弟姐妹一样,把大地上的每一种庄稼当神物,当信仰,他们从骨子里敬畏它们,并深深地感恩。
我再看“指甲姐”付二妮时,感觉自己红了一双眼,也红了一张脸。我听见自己怦怦地心跳。
“有心男”邓大哥说:“这棉朵没全开也有好处哩。”
我好奇地凑过去问:“啥好处?”
他把一个棉朵指给我看,讲解时的神态,活像一位棉花技术员。他说:“你来看,这棉桃才裂开三分之一的嘴儿,从花嘴里掏出的棉花湿乎乎的,还有弹性,棉絮越扯越长,这棉丝就越白亮。这棉花好看又压秤,交到棉花场杨老板不吃亏。要是咱再多下点儿功夫,把满地的棉花都抠完,说不定他还有钱赚。”
我眼睛一亮,说:“真佩服你了邓大哥,不愧是有心男。”
他没听清,问我:“啥?”
没想到,我一高兴就把私自给他起的外号给喊出来了,一边赶忙摆手,一边后退说:“没啥,啊,大哥。”
退到一个年轻女子身边,她正热烈地讲萝卜,声音又尖又细。她说:“在赵老板家,老板娘天天给咱炒萝卜吃,心想,今儿个这杨老板总会改改口味吧,没想到还是萝卜菜,吃得我光在花棵子里放屁,一步一个,一蹲一个,噔噔响。”
“耳环女”莫多多这丫头就咯咯笑,笑声比她还尖锐。那女子一斜眼说:“你这闺女笑啥哩?我这屁,要是能把棉桃子蹦开也行啊。”
(未完待续)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
□阿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