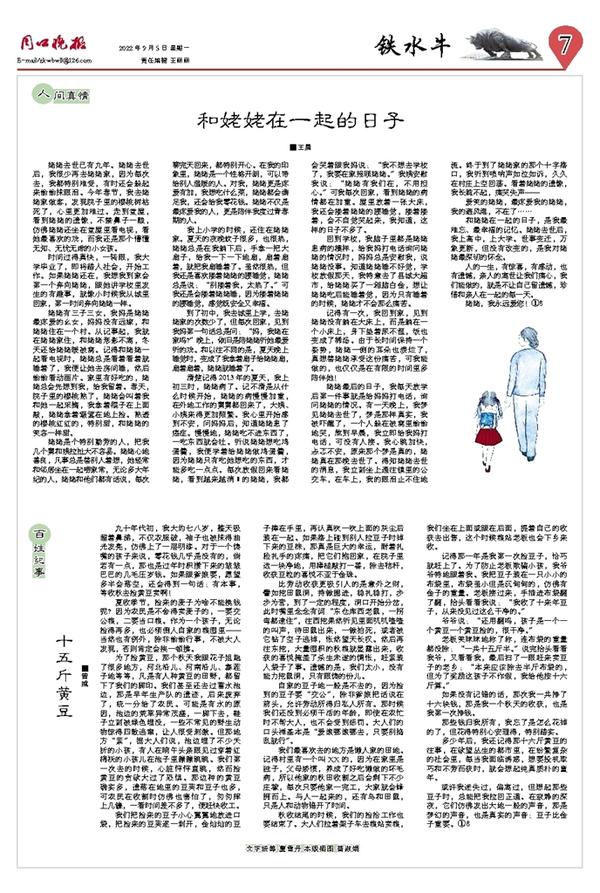■曾威
九十年代初,我大约七八岁,整天吸溜着鼻涕,不仅衣服破,袖子也被抹得油光发亮,仿佛上了一层明漆。对于一个馋嘴的孩子来说,零花钱几乎是没有的,倘若有一点,那也是过年时积攒下来的皱皱巴巴的几毛压岁钱。如果跟爹娘要,愿望多半会落空,还会得到一句话:有本事,等收秋去捡黄豆卖啊!
夏收季节,捡来的麦子为啥不能换钱呢?因为农民是不舍得卖麦子的,一要交公粮,二要当口粮。作为一个孩子,无论捡得再多,也必须倒入自家的粮囤里——当然也有例外,除非偷偷行事,不被大人发现,否则肯定会挨一顿揍。
为了捡黄豆,那个秋天我跟花子姐跑了很多地方,河北沿儿、河南沿儿、寨茬子地等等,凡是有人种黄豆的田野,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。我们甚至还去过蓄水池边,那是早年生产队的遗迹,后来废弃了,统一分给了农民。可能是有水的原因,池边的荒草异常茂盛,一脚下去,鞋子立刻被绿色埋没,一些不常见的野生动物惊得四散逃窜,让人很受刺激。但那地方“紧”,据大人们说,池边埋了不少夭折的小孩,有人在晌午头亲眼见过穿着红棉袄的小孩儿在池子里蹦蹦跳跳。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,心脏怦怦直跳,然而捡黄豆的贪欲大过了恐惧。那边种的黄豆确实多,遗落在地里的豆荚和豆子也多,可农民在收割时仿佛也害怕了,匆匆挥上几镰,一看时间差不多了,便赶快收工。
我们把捡来的豆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,把捡来的豆荚逐一剥开,金灿灿的豆子捧在手里,再认真吹一吹上面的灰尘后装在一起。如果路上碰到别人拉豆子时掉下来的豆株,那真是巨大的幸运,耐着扎脸扎手的疼痛,把它们抱回家,在院子里选一块净地,用棒槌敲打一番,除去秸秆,收获豆粒的喜悦不亚于金珠。
比劳动收获更吸引人的是意外之财,譬如挖田鼠洞,持锨掘进,稳扎稳打,步步为营,到了一定的程度,洞口开始分岔,此时嘴里念念有词“东仓库西老鼠,一拐弯都逮住”,往西挖果然听见里面叽叽喳喳的叫声,待田鼠出来,一锨拍死,或者被它钻了空子逃掉,怅然望天长叹。然后再往东挖,大量囤积的秋粮就显露出来,收获的喜悦掩盖了杀生未遂的惆怅,赶紧装入袋子了事。遗憾的是,我们太小,没有能力挖鼠洞,只有眼馋的份儿。
自家的豆子地一般是不去的,因为捡到的豆子要“交公”,除非爹娘把话说在前头,允许劳动所得归私人所有。那时候我们还没到必须干活的年龄,即使在农忙时不帮大人,也不会受到惩罚。大人们的口头禅基本是“爱滚哪滚哪去,只要别捣乱就行”。
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懒人家的田地。记得村里有一个叫XX的,因为在家里是独子,父母娇惯,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,所以他家的秋田收割之后会剩下不少庄稼,每次只要他家一完工,大家就会蜂拥而上。与人一起来的,还有鸟和田鼠,只是人和动物错开了时间。
秋收结尾的时候,我们的捡拾工作也要结束了。大人们拉着架子车去粮站卖粮,我们坐在上面或跟在后面,提着自己的收获去出售,这个时候粮站老板也会下乡来收。
记得那一年是我第一次捡豆子,恰巧就赶上了。为了防止老板欺骗小孩,我爷爷特地跟着我。我把豆子装在一只小小的布袋里,布袋虽小但是沉甸甸的,仿佛有金子的重量。老板接过来,手插进布袋翻了翻,抬头看看我说:“我收了十来年豆子,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的。”
爷爷说:“还用翻吗,孩子是一个一个黄豆一个黄豆捡的,很干净。”
老板笑眯眯地称了称,连布袋的重量都没除:“一共十五斤半。”说完抬头看看我爷,又看看我,最后扫了一眼赶来卖豆子的老乡:“本来应该除去半斤布袋的,但为了奖励这孩子不作假,我给他按十六斤算。”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那次我一共挣了十六块钱,那是我一个秋天的收获,也是我第一次挣钱。
那些钱归我所有,我忘了是怎么花掉的了,但花得特别心安理得,特别踏实。
多少年后,我还记得那十六斤黄豆的往事,在欲望丛生的都市里,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,每当我面临诱惑,想要投机取巧和不劳而获时,就会想起纯真质朴的童年。
或许我迷失过,偏离过,但想起那些豆子时,总能把我拉回正道。在寂静的深夜,它们仿佛发出大地一般的声音,那是梦幻的声音,也是真实的声音:豆子比金子重要。①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