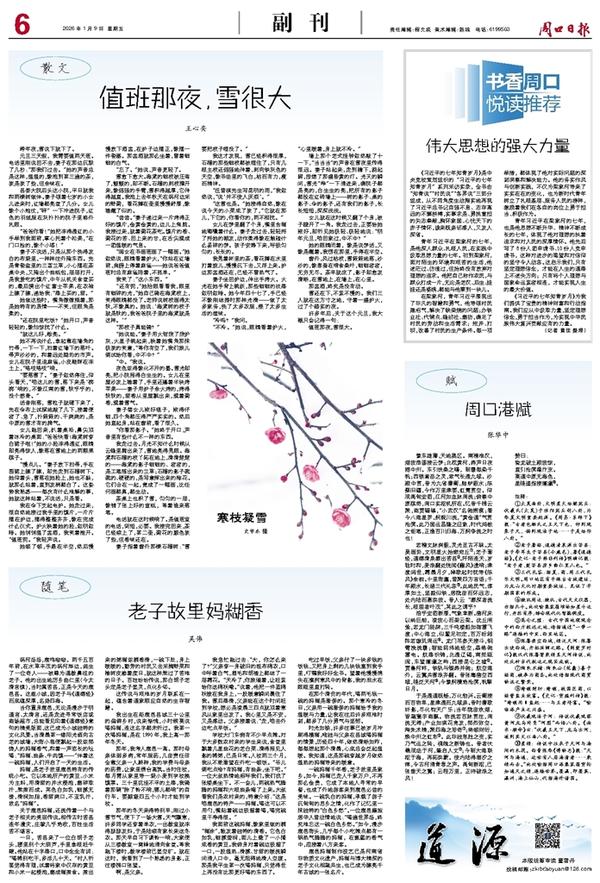跨年夜,雪说下就下了。
元旦三天假,我需要值两天班。电话里刚说回不去,妻子在那边沉默了几秒:“那我们过去。”她的声音总是这样,温温的,像泡到第三遍的茶,淡是淡了些,但余味在。
县委大院后头这小院,平日就我和两棵树做伴。妻子领着七岁的小女儿进来时,红墙都亮堂了几分。女儿像个小炮仗,“砰”一下冲进院子,红色的羽绒服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格外扎眼。
“爸爸你看!”她把冻得通红的小手举到我面前,掌心托着个松果,“在门口捡的,像个小塔!”
妻子不说话,只是从那个洗得发白的布袋里,一样样往外掏东西。先是青瓷盆里的三茎兰草,小心摆在茶桌中央,又掏出个油纸包,层层打开,是我爱吃的馍片,中午从机关食堂买的,最后摸出个红富士苹果,在衣袖上擦了擦,递给我:“路上买的,甜。”
她做这些时,嘴角微微抿着,那是她特有的表情——不笑,但眼角是柔的。
“还在院里吃饭?”她开口,声音轻轻的,像怕惊扰了什么。
“就这儿好,敞亮。”
她不再说什么,拿起靠在墙角的竹帚,一下一下,扫着红墙下的落叶。帚声沙沙的,和着远处隐约的市声。女儿在院子里追麻雀,小皮鞋踩在冻土上,“咯吱咯吱”响。
“要落雪了。”妻子忽然停住,仰头看天,“咱这儿的雪,落下来是‘梆梆’响的,不像江南的雪,软乎乎的,没个筋骨。”
话音刚落,雪粒子就砸下来了,先在伞布上试探地敲了几下,接着便密了、急了,扑簌簌的、干爽爽的,是中原的雪才有的脾气。
女儿跑回来,扒着桌沿,鼻尖顶着冰冷的桌面:“爸爸快看!海棠树穿白裙子啦!”她的小脸冻得通红,眼睛却亮得惊人,像落在雪地上的两颗黑棋子。
“慢点儿。”妻子放下扫帚,手在围裙上擦了擦,却先走到石榴树下。她仰着头,雪落在她脸上,她也不躲,就那么站着,直到发梢都白了。这姿势我熟悉——每次有什么难解的事,她就这样站着,不说话,只是看。
我在伞下支起电炉。她走过来,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馍片,一片片摆在炉边,摆得整整齐齐,像在完成什么仪式。炉火映着她的脸,忽明忽暗。她悄悄温了盅酒,我笑着推开。“值班呢。”我轻声说。
她顿了顿,手悬在半空,然后慢慢放下酒盅,在炉子边摆正,像摆一件瓷器。那盅酒就那么坐着,冒着细细的白气。
“忘了。”她说,声音更轻了。
雪愈下愈大。海棠的细枝被压弯了,颤颤的,却不断。石榴的刺枝撑开来,像倔强的手臂,雪积得越厚,它伸得越直。我泡上去年秋天在涡河边采的野菊,看花瓣在壶里慢慢舒展,像睡醒了似的。
“尝尝。”妻子递过来一片烤得正好的馍片,金黄金黄的,边儿上焦脆。我接过来,就着菊花茶吃。馍片的香、菊花的苦、回上来的甘,在舌尖混成一团温暖的气息。
“闺女在书画班画了一幅画。”她忽然说,眼睛看着炉火,“你站在红墙前,肩膀上停着麻雀——她说爸爸值班时总有麻雀陪着,不孤单。”
我笑了:“这小东西。”
“还有呢,”她抬眼看看我,眼里有细碎的光,“她自己骑在海棠枝上,笑得眼睛都没了。老师说树枝画得太软,不像真的。她说:‘海棠树的枝子就是软的,我爸爸院子里的海棠就是这样。’”
“那枝子真能骑?”
“她说能。”妻子用火钳拨了拨炉灰,火星子跳起来,映着她嘴角那抹极淡的笑意,“等你有空了,我们娘儿俩试给你看,中不中?”
“中。”我说。
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。雪光却亮,把小院照得白生生的。女儿在里屋沙发上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半块烤苹果——妻子用炉子余火烤的,烤得软软的,甜香从里屋飘出来,混着菊香,混着雪气。
妻子替女儿掖好毯子,掖得仔细,四个角都压得严严实实的。然后她直起身,站在窗前,看了很久。
“你看那影子。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里有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
我走过去。月光不知什么时候从云缝里漏出来了,雪地亮得晃眼。海棠和石榴的枝丫拓在地上,清清楚楚的——海棠的影子细细的、密密的,是工笔描出来的兰草;石榴的影子疏疏的、硬硬的,是写意挥出来的梅花。它们合在一起,竟成了一幅画,比任何画都真,都生动。
茶桌上也积了雪,匀匀的一层,像铺了张上好的宣纸,等着谁来落笔。
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。是值班室的电话,简短,必要。我接完回来,茶已经续上了,第二壶,菊花的颜色淡了些,但香味还在。
妻子指着窗外那棵石榴树:“雪要把枝子埋没了。”
我这才发现,雪已经积得很厚,石榴的那些细枝都被埋住了,只有几根主枝还倔强地伸着,刺向铁灰色的天空,像书法里的飞白,枯而有力,瘦而精神。
“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,”我忽然说,“说‘并不使人厌烦’。”
“这雪也是。”她接得自然,像在说今天的小菜咸了淡了,“它就在那儿,下它的,你看你的,两不相扰。”
女儿在梦里翻了个身,嘴里含糊地嘟囔着什么。妻子走过去,轻轻捋了捋她的额发,动作柔得像在触碰什么易碎的梦。孩子安静下来,呼吸匀匀的、长长的。
我晃着杯里的茶,看花瓣在水里打着旋儿,慢慢沉下去,又浮上来。炉边那盅酒还在,已经不冒热气了。
妻子坐回炉边,伸出手烤火。火光在她手背上跳跃,那些细细的纹路忽明忽暗。她今年四十七了,手已经不像刚结婚时那样光滑——做了太多家务,洗了太多衣服,浸了太多生活的滋味。
“冷吗?”我问。
“不冷。”她说,眼睛看着炉火,“心里暖着,身上就不冷。”
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忽然敲了十一下,“当当当”的声音在雪夜里传得很远。妻子站起来,走到檐下,踮起脚,按熄了那盏昏黄的灯。光灭的瞬间,雪光“哗”一下涌进来,满院子都是亮的,白生生的亮,把所有的影子都投在红砖墙上——树的影子、桌的影子、伞的影子,还有我们的影子,长长短短,深深浅浅。
女儿就在这时候又翻了个身,被子蹬开了一角。我走过去,正要给她掖好,却听见她极轻、极轻地说:“明年元旦,咱回家过,中不中?”
她的眼睛闭着,像是说梦话,又像是醒着。我愣在那里,手停在半空。
窗外,风过枯枝,雪簌簌地落,沙沙的,像春蚕在啃食桑叶,细细密密,无穷无尽。茶早就凉了,影子却愈发清晰,在雪地上,在墙上,在心里。
那盅酒,终究是没有动。
雪还在下,不紧不慢的。我们三人就在这方寸之地,守着一盏炉火,过了个踏实的夜。
许多年后,关于这个元旦,我大概只会记得一句:
值班那夜,雪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