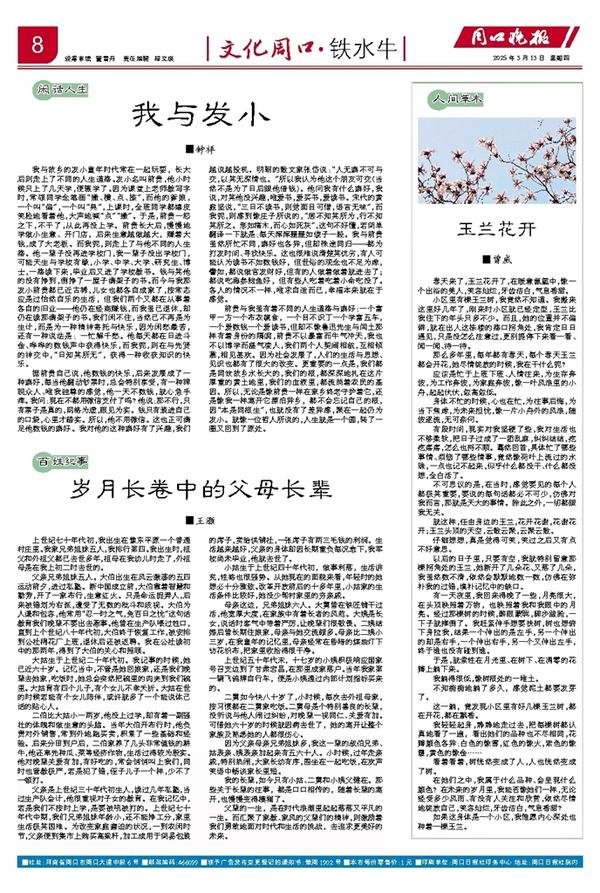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出生在豫东平原一个普通村庄里。我家兄弟姐妹五人,我排行第四。我出生时,祖父和外祖父都已去世多年,祖母在我幼儿时走了,外祖母是在我上初二时去世的。
父亲兄弟姐妹五人。大伯出生在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前夕,进过私塾。新中国成立前,大伯靠着智慧和勤劳,开了一家布行,生意红火。只是命运捉弄人,后来被错划为右派,遭受了无数的批斗和歧视。大伯为人谦和包容,他常用“忍一时之气,免百日之忧”这句话教育我们晚辈不要出去惹事。他曾在生产队喂过牲口,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大伯终于恢复工作,被安排到公社棉花厂上班,退休后还被返聘。我在公社读初中的那两年,得到了大伯的关心和照顾。
大姑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。我记事的时候,她已近六十岁。记忆当中,不管是她回娘家,还是我们晚辈去她家,吃饭时,她总会突然把碗里的肉夹到我们碗里。大姑育有四个儿子,有个女儿不幸夭折。大姑在世的时候若能有个女儿陪伴,或许就多了一个能说体己话的贴心人。
二伯比大姑小一两岁,他没上过学,却有着一副强壮的体魄和做生意的头脑。当年大伯开布行时,他负责对外销售,常到外地跑买卖,积累了一些基础和经验。后来分田到户后,二伯家养了几头非常值钱的耕牛,他还率先种瓜、菜等经济作物,生活过得较为殷实。他对晚辈关爱有加,有好吃的,常会悄悄叫上我们,同时也管教极严,若是犯了错,侄子儿子一个样,少不了一顿打。
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生人,读过几年私塾,当过生产队会计,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。在我记忆中,若是我们不按时上学,是要被吼被打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们兄弟姐妹年龄小,还不能挣工分,家里生活极其困难。为改变家庭窘迫的状况,一到农闲时节,父亲便到集市上购买高粱秆,加工成用于简易包装的席子,卖给供销社,一张席子有两三毛钱的利润。生活越来越好,父亲的身体却因长期重负每况愈下,我军校尚未毕业,他就去世了。
小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,做事利落,生活讲究,性格也很强势。从她现在的面貌来看,年轻时的她想必十分雅致。改革开放前后的十多年里,小姑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,她没少帮衬家里的穷亲戚。
母亲这边,兄弟姐妹六人。大舅曾在铁匠铺干过活,他宽厚大度,在家族中有着长者的风范。大姨是长女,说话时客气中带着严厉,让晚辈们很敬畏。二姨结婚后曾长期住娘家,母亲与她交流颇多。母亲比二姨小三岁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母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花织布,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十七岁的小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支边到了甘肃宕昌,在那里成家落户。当年我家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,便是小姨通过内部计划指标买来的。
二舅如今快八十岁了,小时候,每次去外祖母家,按习惯都在二舅家吃饭。二舅母是个特别善良的长辈,没听说与他人闹过纠纷,对晚辈一视同仁、关爱有加。可惜她六十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,她的离开让整个家族及熟悉她的人都很伤心。
因为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多,我这一辈的叔伯兄弟、姑表亲、姨表亲加起来有五六十人。小时候,过年走亲戚,特别热闹,大家长幼有序,围坐在一起吃饭,在欢声笑语中畅谈家长里短。
我的长辈,如今只有小姑、二舅和小姨父健在。那些关于长辈的往事,都是口口相传的,随着长辈的离开,也慢慢变得模糊了。
父辈的一生,是在时代浪潮里起起落落又平凡的一生。而汇聚了家教、家风的父辈们的精神,则激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时代和生活的挑战,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。